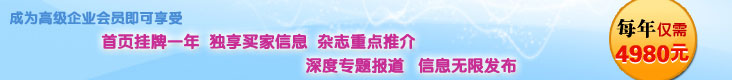第一个问题,无论什么样的应急事件发生,政府永远是总指挥。政府在这个总指挥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指导或者是指挥供水企业来应对这个水危机这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如果这个企业已经市场化了,那么政府还能不能指挥这个企业来应对这样的危机?
第二个问题,在水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公众、政府是不是能信任我们已经市场化的企业?他是不是能够在丢弃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来应对这个危机?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现在出现了一些呼声,我们供水行业(不是污水行业)不能够进行市场化,这个声音还是比较大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危机中各方的责任到底怎么确定?政府和企业、公众到底是怎么样的责任?比如哈尔滨的停水事件,如果是已经市场化的企业,这个停水是由政府来做这个决定还是由企业来做这个决定?如果是污染的水源已经被污染了,不能够达到水源水的标准,我们的企业有没有权利停水?这个信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由谁来向社会发布?在这个过程中显然政府和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和看问题的角度会不同的。比如这次哈尔滨事件最早的公布停水并不是水污染事件而是借口是检修。这样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企业都带来了显著的社会不信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形象,如果说是政府要求企业必须按照政府的意愿去发布的话,我们企业是不是要这样发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水污染之后,为了保证供水的连续性,我们必须在水源不达标的情况下进行临时性的应急的技术方案来进行供水,这个技术方案是由我们供水企业自己来定这个技术方案还是由中国、地方政府组织专家组来制订这个方案?如果这个方案出现了分歧听谁的?这都带来了一些问题。其实哈尔滨最初公司出的技术方案和后来专家组的技术方案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用颗粒活性炭,一个用粉末活性炭,后来证明用粉末活性炭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保证了哈尔滨四天的供水,否则哈尔滨是不可能四天供水的。万幸的是我们这个方案是可行、安全的,如果说这个方案出了问题,这个责任谁来承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还有一些问题就是供水企业如果说因为停水,必然会带来一些连带的责任。企业是不是要承担这样一个连带的责任?比如还是松花江的事件,我们万幸的是在哈尔滨停水四天的时候没有发生火灾,如果一旦发生火灾,所有的管网没有供水能力,后果不堪设想,可能我们这个哈尔滨城市不会再存在了,这个风险非常大。那么相应的这个连带责任由谁来承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并不是我们在决策的过程中所有的决策都是正确的,有相当的决策是由于信息的不准确或者判断的不准确或者准备得不充分,有些决策是错误的。那么这个错误的决策是谁来承担,政府还是企业?这里面涉及到一系列的危机中的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危机中的经济责任谁来承担?是政府的公众的还是企业的?另外一个引申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水源的高污染发生的时期,我们在对水业投资的时候是不是对周边环境做一个风险分析,来规避企业出现这样的风险。无论是发生什么样的风险,无论是政府给你什么样的补偿,发生风险毕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风险评估来作为投资风险的一部分?这是我们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因为时间问题不在这里一一介绍。
下面想对这里面的几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讨论。[TAG][PAGINATION][/PAGINATION][/TAG]
第一个是关于安全性的问题,我们水安全在市场化的企业里面到底是安全还是不安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说我们从哈尔滨这个供水事件以后引伸的,而是从水业投资多元化后在国际上就一直争论的一个问题。从目前国际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案例研究结果来看,水市场化并没有降低公共供水安全,就是说安全不安全跟市场化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现在大家看到的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就是从我们国家近期的污染事件来看,如果这个公司是我们政府自己的,是自己政府能控制的,但是也没有执行上报的制度。我们水厂停水也好,还是水源地出问题也好,并不是我们政府或者政府控制的企业逐级上报,没有上报。而恰恰是我们已经市场化的企业,不是当地政府能控制的企业把这个情况上报了。因为他必须上报,不上报责任都在他这里,他会更敏感,就必然要上报。是不是处理供水危机过程之中,我们政府控制的企业公众就信任呢?现在看来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政府和公众和这个企业,如果在这个过程之中没有交待实情的话,危机过后,公众的信誉度不是因为你这个企业是政府管理的公众的信任度就高。哈尔滨供水事件之后,也有一段时间公众用水量一直持续到比较低的水平上。
第二个问题关于责任和费用的问题,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污染事件或者社会危机发生之后,都不是单方的责任,必须全社会携起手来共同面对。这样就意味着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公众都有责任、义务来应对这样一个全社会面临的危机。首先认为第一个就是各方要有明确的、共同承担的责任。如果这个事件是由于污染事故发生的,污染者是最主要的责任者和费用承担者,这是我们应该处理这样的事物的一个原则。但是如果危机发生是由于自然造成的或者是由于无法追究事故责任人,比如说SARS、罢工,我们就应当采取政府和供水服务机构的一个共同负担的机制,就是政府给予补贴,但是企业也要承担一定的成本。OECD国家,还有英国的水工业法案,美国环境响应以及补偿法案以及美国的应急预案都在供水行业遇到这个危机的时候,各方应该有什么样的责任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大家可以查相关的资料,非常全面,不尽相同但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详细在这里谈具体的责任和费用了。
具体的想强调一下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按照OECD国家的要求,所有的应急事件,污染责任单位要对应急的行动付费。南非的国家水法案也提出了同样的一个要求。这里给大家举几个案例,第一个案例这是我们水污染事件里面的一个案例,1986年11月1日在瑞士发生了一次比我们松花江还要严重得多的污染事件,一个化工农药厂爆炸,大量的化学品进入到莱茵河,流经几个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事后这家化学公司对德国、荷兰都分别进行了赔偿,赔偿包括各个方面,其中对于供水企业损失的赔偿,德国大概是200多万,荷兰因为到下游了比较少是7.2万马克,包括替代水源的成本、关闭供水系统的成本、水质分析成本、以及处理的额外的成本。
我最近又把今年二月份国际上由于污染事件造成损失的一些案例在这里给大家罗列一下,时间关系不一一介绍。
这些都是因为各个公司对环境造成了危害,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处罚和赔偿。比如说壳牌公司的还有一些其他公司的在这里不一一介绍。中国情况按照中国的水污染防治法有明确的要求污染者付费的原则,但是能不能做呢?我们有困难。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细则里面明确规定,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事故,只能按照直接损失的30%进行罚款,而且最高限额不能超过100万,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我们显然不能通过这样一个机制来解决费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