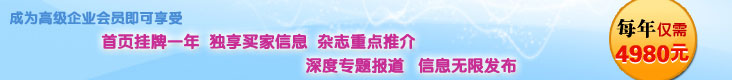供水短缺!水体污染!在这场工业时代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水危机面前,本届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发展部长级论坛和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大会给出了鲜明的主题。大会的综合论坛上,亚太地区一流的学界、企业、组织和政府的代表,带来了最前沿、最崭新的经验……
世界银行能源、交通与水局
局长Jamal
Saghir: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在水处理方面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融资,帮助中国在水务上的不断改革。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在城市水供给和水污染治理方面发展非常迅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迫切地想使各自的供水设施变得更为有效,中国也不例外。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一些省份的水务设施建设开始从公共运营转为私营,如何使这种转变变得更好呢?
首先,在转变中必须注意倾听和了解消费者的要求,保证社会的接受度。以前这一点很少受到重视。其次,需要利用市场的激励机制,吸收社会资本的参与运营。再次,就是要建立一个很好的水务结构,这是核心的问题。不仅要使市场受益,也要加强和发挥政府的引导性和控制力。最后是政府对水务项目的开发,要有综合的计划,加强效率和投资。
中国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
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当前正面临着一场越来越紧迫的水危机,它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源性缺水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是水质性缺水的问题也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怎么应对这场挑战?不可忽视的是在技术上,在工程方面要做些什么。
第一、通过多源供水,确保城市饮用水安全。城市是整个国家的命脉,据统计,80%的GDP、50%的人口、90%以上的科技创新都集中在城市,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浓缩在城市之中。我们要强化地下水源管理,采取封而不死、整体接管、严格维护、应急启用的措施,在城市密集区采取区域联供,确保饮用水安全。
第二、城市防洪疏导法优于堤坝建设。城市防洪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和避免洪水的灾害,而不是简单地抵抗洪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告诉我们,提高城市的防洪能力的标准应该是河道容纳洪水的标准,而不是抗衡洪水的标准。不能盲目追求防洪堤防洪能力“××年一遇”的误区。此外,防洪工程应当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的文化。
第三、污水处理设施应当规模适中,分散布局。中国许多城市,在治污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大截排”的教训。对此,国际水协早在10年前就提出了“规模适中、分散布局、深度处理、就地回用”的技术导则,人们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污水处理,至今深得其益。
第四、加快雨污分离管道网的改造。除了部分城市新区实行了雨污分离外,我国其它大部分城市的老城区还是雨污合流,从而导致了污水处理厂进水COD浓度偏低。另外,一些城市不分青红皂白,沿着城市边缘排污口简单地使用截排工程,这无助于污水防治。对此,国家“十一五”国债将优先安排雨污分离的污水收集工程资金,将采取污水处理费返回与COD消减量挂钩的激励措施。
第五、污水处理应从末端向源头转移。大力推行工厂水、尤其是有害的废水排放工程的“零排放”是当前要务。原来的方案是把工厂的污水跟新水混合在一起,去除有害物质。现在应当把新水中有害的物资进行单独处理,不把它放到城市的污水系统中,而城市的污水经过深度处理以后进行有效的再利用。
第六、推广“四节一减”型除磷脱氮和其它水处理技术。我国各地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自然水体富营养化问题,其中磷、氮污染是主要的原因。传统的脱磷除氮的工艺和传统的水处理流程,包括设施、净化水处理的流程亟待改进。斜板沉淀、膜工艺、生物除磷脱氮和积木式紧凑型水处理单元应得到大力推广。
第七、城市水资源多层次循环利用,促进城市节水。首先是推广节水器具、制定阶梯水价。其次是认真设计建筑节水单元,注重小区的中水就地回用。再次是重视城市河道生态补水与循环供水。最后要尽量避免长距离调水带来高昂的工程、生态和社会成本。
第八、雨水利用——低冲击开发模式。日前济南等城市突降暴雨,造成了洪涝灾害,这个教训告诉了我们,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是应该适应洪水,而不是简单地抵抗洪水。应扩大城市可渗透面积,多途径进行雨水收集利用,多层次实施废水再循环使用,保护和利用原有的水体和植被。
第九、水生态修复。一个水生态如果良好,它能自动降解和消耗污染。而水生态是死的,反而自动增加水体的污染。因此,应谨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原则,将水生态的修复看作治水的根本之道。
第十、流域污水联动治理。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社会中每个行业、各个政府都有节水减污的义务。但因分工、具体用水方式和所处流域空间地理不同,协同治水是第一要务。
我们各级政府和广大科技人员,如果将未来七年的重点和技术创新集中在以上这十个领域,我相信,我们将会取得成功。
国际水协主席
David
Garman:
源控制,不仅仅是简单地来保护水的源头,而是需要进行生态方面的重置,然后实现所确定的目标。由于中国现在很多的水源都是多重使用的,我们需要把多领域、多用途的水进行平衡,其中还包括未净化水的质量控制,以及降低处理的成本。
我们同样要保证能够对水体进行长期的控制、保护和监督。而世界上的先进经验告诉我们,给水控制要在10到40年之后才能够收到成效。环境状况的这种可变性,要求进行大量的投资才能进行监控,来保证环境状态的一个稳定性。如何在这些方面达到理想的效果呢?
首先,对水体营养控制,我们需要微生物来进行水源处理,同时还需要增加化学制剂。另外一个是脱氮措施,但脱氮的费用比较高,而且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购买设备。
其次,对于供水的污染,可以采用“锁磷”的方案来应对,该方案通过一个快速、稳定的方式,限制磷在水体营养物中的比例,让水质变得更加清澈。
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
水是生命之源,但是我们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水危机,主要包括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两大方面。其中,水污染就会加剧水资源的短缺,造成水质性的缺水。所以,水污染是水危机的一个核心问题。
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一下自己,20多年来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做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收效却很小?为什么现在污染还如此严重?今后究竟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是值得大家深思、讨论和琢磨。我自己认为这里有三大原因:第一,没有按照科学发展观办事。第二,没有按照法律办事。第三,没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对我国水污染防治对策,我讲一些自己的想法:首先,必须要从提高全民、特别是从提高各级领导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着手,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完全协调起来。其次,我们必须加强法治,必须要注意严格执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再次,我们在制定规划的时候,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情,污水处理厂跟污水管网必须要配套建设。同时,我们还要切实地进行工业结构的调整,严格控制和加快淘汰或者改造这些高消耗、高污染的企业。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潘文堂:
五年前,中国的水务主题一个是资本,一个是机制和体制。而今天,中国水务的主题已经由资本和所谓的机制转移到污染问题,而污染又是一个企业难以独自完成的任务。
应当说,水污染防治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也面临着一个直接的问题,即不同城市、不同地域之间的协调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建议国家应该从区域和流域的角度,建立相应的职能部门,对企业和社会实行统一的管理。
当然,关于流域性治理国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目前关键的问题是要有一个承担的主体,如果能在一个区域内形成一个以大企业为首的主体,由主体按照区域、流域的要求,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实现统一的水污染防治,这个作用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
清华大学副校长陈吉宁:
我们现在的环境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需要城市联动来解决,所以需要我们从更高层面来看这个问题。
水流域的管理,是一个跟自然区域相关联、涉及到多个利益相关者和需要可靠的科学理论指导支撑的管理,具有跨部门、跨区域和跨学科的管理内涵。因此,空间发展不平衡,缺少区域性的经济主导,流域层次上的经济、产业、土地规划和环境政策缺失,将大大限制对水流域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