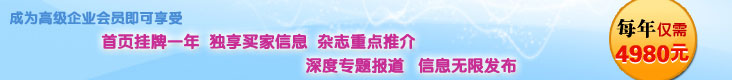面对地方经济利益的强大力量以及环保执法权力的有限空间,如果不及时进行制度性扩权,中国未来的环境部,即令换了帽子,其既往面临的捉襟见肘的尴尬恐怕仍然难以消失。
中国“两会”期间公布了将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的计划,无疑给缓解日趋严峻的环保形势增添了一抹曙光。在几位省部级地方大员拿官职作为“节能减排”达标的承诺抵押之后,中国政府关于扭转既往发展模式的决心,再次收获更多的证明。
国际义工组织者、丹麦人Lotte还记得她
1990年第一次来中国时的场景:站在浦东的地头,和她对话的,不是今日在各个跨国银行供职的匆匆白领,而是荷锄耕地的江南农夫。彼时的Lotte想象不到,中国之后的18年,会发生这样惊人的变化。此时的中国,正在为如何扩大对外出口想尽办法,不像今天正为过量的顺差担心。
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中国创造了世界公认的经济奇迹。然而,这个向来对环境和气候极为依赖的农业国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却令人痛心地陷入环境高危状态——在消耗了数量惊人的煤炭、石油、钢材以及水泥等建材后,中国创下了另一个记录: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到10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
面对地方政府气势如虹的增长需求,环保部门的令箭或提醒,常常被更强的呼声所掩盖。在各个诸侯的经济“军备竞赛”当中,官员由地方任命的地方环保机构或者保持沉默,或者“协助”通过有关环境测评。而在北京的国家环保总局,面对地方经济的破坏型扩张群像,焦急之中,手段有限。
国家环保总局的高级官员曾向有关媒体证实:被中国先民列为四大母亲河的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几乎所有支流要么坏死,要么干涸;9个大湖,7个的水质已是五类以下。而大城市集中的华北平原地区,则形成了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大漏斗。
环境风险高发期在中国人均收入远远不及西方之时,提前来临。著名的松花江污染,几乎酿成国际性事件。其后,水污染事故几乎每两天一次的速度发生。大批分布在江河湖海左近的污染性工业项目,令中国业已脆弱生态处于危险的包围之中。
恶化的环境,令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空前的压力。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前提下,节能减排,减少环境污染,已成为须尽快完成的作业。
在经济发展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之后,中国试图将其飞速的增长快车纳入健康的方向。3月11日公布的中国内阁改革方案中,主管环境保护的国家环保总局计划升格为环境保护部。在众多或合并或削权的机构调整声中,环境部的高调升格令人瞩目。这是中国在本国环境态势已退无可退的境地下,做出的危机抉择。中国环境部的亮相,既让国际社会期待,也让观者暗自担心:几百人的编制,面对如此广泛、复杂的环境透支能否胜任?
在官方开始采取战略性措施扭转中国环境的危险现实之前,形式多样的民间机构已经开始在为恶化的环境预警或干预。普通百姓也意识到,环境生态问题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不能听之任之。被认为是中国公民社会逐渐发育的几个标志事件,比如非政府组织在怒江大坝项目上的干预行动,厦门PX项目风波,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延长项目的和平散步活动,提前在民间推动了对环保问题关注的预热。手段相对有限的国家环保总局对于民间力量介入环保,曾表示了罕见的欢迎。环保总局的官员也高调表示,NGO是环保部门的天然盟友。
相较于民间环保力量的风生水起,官方监督机构的力量则显得长期亏缺。幸运的是,此次发展政策调整,已被列入中国统一的战略规划。刚性的节能减排指标被分到各省的考核指标之中,因危机而产生的压力传递透过中国紧密的行政系统,应能产生巨大的调试效应。
然而,中国增长模式的改变,尚需相当的时间或金钱成本。而中国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现实,使得产业淘汰更新显露出由东向西迁移的痕迹。在沿海业已富裕的地区提升门槛、逐步把可能带来环保麻烦的粗放型企业淘汰出局时,或许在欠发达的西部,正是地方部门欢迎的新经济增长点。
即使在沿海地区,一些能给地方GDP带来增益的大型项目,在官员有限的任期内,匆匆上马,以尽快形成政绩。广州南沙的石化项目,因未经环境测评便露出上马迹象而受到当地媒体的批评。环保部门在此风波中的缺位,再次传递了令人担心的信号。
目前人数只有美国环境署六十分之一的中国环保部,在获得更多扩权,特别是获得针对地方行政决策的有效否决权之前,要扮好中国环境监督领军者的角色,显然十分困难。
中国环保,必须升格与扩权同步。这种扩权,一方面是为官方的环境保护部授予更多的有效行政手段,包括对地方立项的一票否决;另一方面,则应向来自民间的环保行动提供更大话语和活动空间,以形成广泛的监督网络,填补官方监管的空白点。